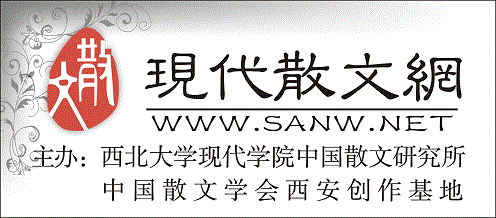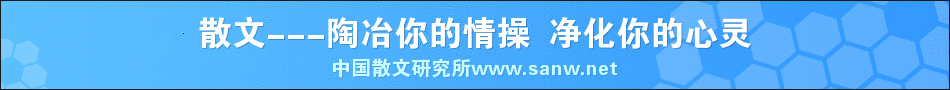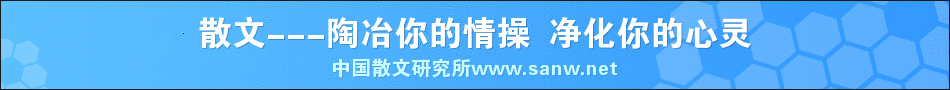想起了《跳蚤之歌》
记得俄罗斯经典作曲家莫索尔斯基,曾经给德国大诗人哥德的一首叫《跳蚤之歌》的诗谱过曲,后来成为流传各国的世界名曲。四十年前、上世纪6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音乐厅每周一次的星期音乐会上听过上海音乐学院温可铮教授演唱这首名曲。温可铮是我国首屈一指的男低音歌唱家,直至今天,他那低沉的带着嘲弄的声音和浑厚的
闪着调笑的目光,仍然烙在我心里。《跳蚤之歌》意思和《皇帝的新衣》有些相近,说的是国王宠养了一只跳蚤,让裁缝给它做了一件大龙袍,封了宰相,挂了勋章,很得意了一阵子,最后被人捏死了。
《美文》杂志从梳理散文写作历史的角度出发,约我就“形散神不散”写点文字,顺便也对当前散文创作谈点看法,却之既然不恭,不如应命。正琢磨着如何开头,不知怎的就想起了这首《跳蚤之歌》。
真相及本意
44年前的5月,我是大三的学生,斗胆投稿《人民日报》副刊“笔谈散文”专栏,写了那篇500字短文《形散神不散》,接着别人的意思说了几句即兴的话。在名家林立、百鸟啁啾的散文界,这几句话是连“灰姑娘”和“丑小鸭”也够不上的,不过就是一只跳蚤吧,不想渐渐在文坛、课堂和社会上流布开来。
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处在“文革”运动中的我下放在农村、工厂,辗转于县以下的基层单位,离文坛何止十万八千里,对于这句话广为流传,并作为散文的“特征”,上了各种教材,还选为1982年高考试题,一概浑然不知。后虽有所耳闻,也只是微风过耳,并不在意。直至1982年6月四川大学中文系曾绍义老师从《文艺报》上逮住了我的地址,专门就这件事给我来信,我才知道了较为确切的情况。接着便开始有了争议,陆续读到了一些文章和报道,也应邀浅尝辄止地参与了一点讨论。在1982年7日月给曾绍义老师的回信和1987年10月发在《河北学刊》的文章中,大致可以看出自己当时的态度,归纳起来主要是这么3点:
一、 说明自己对于这点小感想能引起如此长久的反响和不大不小的风波,实在始料未及,而且“担待不起”。也就是文章开头说的“跳蚤”心情、灰姑娘心情吧。
二、 说明那篇小文并无给散文写作提要求、定规矩之意,只是在参与《人民日报》“笔谈散文”讨论时,从一个侧面提供一点感想而已。在中国,散文的水太深了,各种类别、写法太丰富多彩了,谁吃了豹子胆,敢用三五百字来给它总结特征?比如那种记叙一人一事的散文,就可以采用形神都不散、都聚焦的写法,用“形散神不散”怎么能概括散文的百态千姿呢?我的本意,主要是针对“形散”一类的散文来说的,提醒一下作者,形散可以,但神不能“散”。
三、 澄清那篇小文的重点并不是后来有人说的,是主张散文不能写散,要写得集中,恰恰相反,我是接着老作家师陀说散文“忌散”,开宗明义提出散文“贵散”,主要谈散文贵散的。文章开始,关于神不散,只用“不赘述”一笔带过,后面便以鲁迅的文章为例,谈形要散,又如何散法。
四、 但我仍然坚守“形可散,神不可散”。如何对待“神不散”,这是我在《河北学刊》文中与林非先生讨论的焦点。我们的分岐,主要是一、如何理解“神”?林非先生是立足于60年代对散文之“神” 的狭隘理解(即主题和中心思想,这也是我当时的理解),来批评“神不散”的,我则觉得随时代的变化,应对散文之“神”作更宽泛的解释(如意蕴、情绪、甚至一种心理场),从这个意义上,“神”是不能散的。二、如何理解“散”?林非先生说,“为什么‘神’只能‘不散’呢?事实上一篇散文之中的‘神’,既可以明确地表现出来,也可以意在不言之中,”也就是说,他认为“神散”属于表述范畴,即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现“神”,因而“神散”可以成立。而我则认为,“散神”是散文精神层面的问题,实质是“有神”还是“无神” 的问题,而不是如何表现神的问题。销解“神”是不可以的。恕我在这里不再详说。
争议是必然的
“形散神不散”在上世纪80年代引发争议是必然的。
首先是80年代初社会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想解放的必然,是散文观和散文写作实践在新的春天萌动、苏醒、要求自由空间的必然。任何一种解放,有一个前提要求,便是明确要挣脱的束缚是什么, “形散神不散”便历史地成为了那个时代散文写作要挣脱的一个词语。为什么它会成为60年代束缚散文写作的标志词语呢?
一、 因为它的确没有跳出特定时代左的和形而上学文艺思想的阴影。比如,开始我把“神不散”,形而上学地理解为“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从举的几个鲁迅的例子也能看出我对散文形、神理解的肤浅和简单。这都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二、 因为它表述的明快和传播的广泛,使它事实上成为那个时代关于散文写作极具代表性、因而可以作为靶子的一句话。当然又正因为它只是一句话、一篇几百字短文,作为科学论断远不充分,先天地为批判留下了空间,留下了便捷。
三、 因为那个很强调社会功利、政治功利的时代给它增加了一些负面的附加值,赋予它一些原文没有的内涵,而这些内涵正是改革开放后散文写作要冲破的一些东西。比如原文主张“散文贵散”误传为主张散文不能散,又将“神就是主题”强加于那篇短文。而原文强调“神不能散”又误传为要为政治服务,要直奔主题、图解政治、配合中心,等等。这还不应该批判吗?
四、 还因为这个说法在当时已经客观地和一些当局提倡的、成为当时样板的散文作家群体,如杨朔、刘白羽们联在了一起,成为一种理论和创作互相印证的散文现象。杨朔那种特定的创作现象补充了、也又一次朝左的方位上引申了这个简单的论断。
跳蚤一旦被人强制穿上龙袍、戴上勋章,“形散神不散”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被人认为是散文写作旧秩序的反映,被人认为是束缚新时期散文写作的框框,也十分必然的而且合理了。
那以后,西方种种新的文化哲学、美学、文学、散文的思潮和创作长驱直入,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散文观和散文写作面貌。前卫思维和新锐写作,更是以它私人话语的情致、特立独行的反思和放任不羁的写法,大幅度突破了原有的精神秩序和散文方式。市场经济时代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群体人文素质和个体精神追求的冲击,散文的消闲化、娱乐化和某些领域的功能化、趋利化(如广告散文)都导致了单一的“形散神不散”时代的终结。到了网络散文,写作的那种私密性、互动性、随机性和青春感,那种和最新的日常口语丝毫不隔的“说话文体”,不但早已冲决了“形散神不散”,也几乎冲决了所有的传统散文章法和写法。
所有这些来自新的生活和创作实践的冲击,无疑都是散文顺应时代的新尝试、新探求,都给中华散文增添了新的营养,是一种时代进步。但也要看到,所有这些新的实践,又无疑都只是散文写作多元格局中新的一种,它们不可能取消、取代中华散文文化丰厚的传统和多彩的积累。散文告别了一统江山,进入了多元共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一种散文方式都会有自己的市场,因而都会有作者去耕耘,也都会有各自感到满意的收获。
恐怕正因为如此,近20年来虽然不断质疑、排拒“形散神不散”这个说法,直至今日,采用“形散神不散”老写法的散文(当然只是指写法,而不包括左的时代加于它的那些内容)仍然不衰,相当一批“形散神不散”年代的作家作品至今也还有读者,一版再版,在散文发展史上依然有着应有地位。各种写作方式都拥有自己的读者,散文也才会拥有最大多数的民众,才会满足广大民众对散文之美多方面的需求。其实,这也是“大散文”的一个含义,在这个全局性的、接受学的维度上,散文也的确有大、小之别。
因而,我总觉得问题主要不在写法上,而在思想意蕴方面;不在神要不要散上,而在你那文章里泛漫的是什么样的神,这神又是怎么个表达法。
极有意义,也有坚守
上面谈了一些关于“形散神不散”的背景和研讨情况,也谈了它受到质疑的必然性,要特别指出的是,我虽然澄请了一些具体情况,但从宏观上看,新时期的这场讨论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通过研讨,廓清了附着在这个论断身上的60年代文艺思潮对散文写作的影响,颠复了杨朔式的用政治矫情替代生命实感、用人物、事件、场景、抒情来图解主题的写作路子,整体上把散文写作从千人一面、定于一尊、为政治服务的阴盖下拉了出来,中国的散文进入一个开阔而自由的天地,艺术家的创造生命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有人说,这场关于“形散神不散”的讨论,是文革后散文创作拨乱反正、更新观念的重要事件之一,是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确有一定道理。
在散文写作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一切都过去了,“形散神不散”说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应该让它进入历史了,还是让它沉淀到历史的烟尘之中去吧。
但就这五个字本身论,我还有一些东西要坚守。
当洗尽涂在它身上的“60年代色彩”,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其实,散文的神能不能散的问题,正像一位散文家说的,“是一句寡话”,是说了差不多等于没有说的话。王祥夫是这样说的:“形散神不散是句寡话,小说难道能令其神散?什么文章能令其神散?”“神非主题也----起码对散文而言,神不单指主题。”说得真好!
在当下的散文家中,有多少人都表述了散文得有“神”,“神”不能散的意思,这里我随手从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散文研究》中摘出几段:
贾平凹:“智慧是人生阅历多了,能从生活里的一些小事上觉悟出一些道理来。这些体会虽小,慢慢积累,就能透沏人生,贯通时事。而将这些觉悟大量地用到作品中去,作品的质感就有了。”“这种散文看似胡乱说来,但骨子里尽有道数。我觉得这才算好散文。”
南帆表示同意贾平凹这种看法。他还说,“大散文似乎又要回到文史哲浑然一体的时代”。说,“罗兰 . 巴特的卓越之处在于,深刻的理性与日常景象天衣无缝交汇在他的笔下。中国当代散文思想含量的增加与这些大师的作品有关。”
林贤治:“散文是人类精神生命的最直接的语言文字形式。……失却精神,所谓散文,不过是一堆文字基础,或者一个收拾干净的空房子而己。”他还谈到了形与神的关系:“形式的革新,原本便是精神鼓动下的文字哗变。”不但形式会积淀为精神,而且首先是精神引发形式与文字的革新。
高建群:“散文家要从这一堆素材中,寻找的是立意,是命意,是新鲜的意境和道理。”
杨文丰:欲写散文,必先学会思索。散文之境界,全赖深刻的思考出之。
刘谦:“散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发乎心止乎神。”
当然,今天这些认为散文得有“神”、不能散“神”的看法,是建立在对散文之“神”更宽泛、更深湛的基础上的。“神”不完全是主题,是文章的意、蕴、情、气、韵、场,也包括哲理和潜感觉。时代的进步开拓了我们对散文之“神”的理解,这种认识的提升,反映了中国人精抻生活日渐开阔和丰富的历史进程。
如若以对“神”这样的理解,我们来说散文不能散神,可不真是一句众所公认、无须说的话,一句寡话!
一句寡话,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竟然引发了整整四十年的议论!原因在我们前面说的,争论这个议题,其实争论的不是议题本身,而是附着在这个议题中的时代思潮,时代散文风尚和散文观念、欣尝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讨论它、反思它、抛弃它都是应当的,有意义的。一切为了散文的前行,为了散文的自由和提升。
散文的发展繁盛使它苍白
看看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发展的步伐吧,从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到人文人道人性的渲泄;从人人都用那种本质化的群体人称来写作,到具有生命真实的个体人称的写作,即由“们”到“我”的转变;从精致华丽的唯美唯情的小资写作,到简洁明快即时随心的网络写作、短讯写作;从玄示思考、卖弄文化、狂欢语言的写作到说话散文、对话散文、视听散文的流行……。
看看今天的散文创作实践吧,不但语言----在校园散文和网络散文中,新语汇、新句式是那样地层出不穷,像“风俗得一塌糊涂”,“沉思的气味有一点淡淡的苦”这样的句子,对语言的意蕴、张力、弹性、通感和文化心理内含的发掘和发现是那样的深广。
不但写法----如吴亮那篇几乎在每句话后都用括号添加内容的《咖啡馆》,如洁尘和穆涛们那种以一枝极为散漫的笔去写散漫的城市生活,只是不经意地置放到一定的关系中,平淡中就有了一点寻味,有了一点心不在焉的经心,有了一点捉摸不定的感觉的妙文。
还有贾平凹那永无穷尽地、饶有深意地比喻。还有前卫散文中那些把事物推向极至、推向异态、推向负数、推向不可能,然后烙在你心里的各种恶喻,像“女人的鞋跟在安静的小巷里踩出勃朗宁手枪的射击声”之类。
还有,你觉得那些和散文根本无缘的东西,现在都成了绝好的原材料,写出了绝好的文章。“炒股智慧”、“符号逻辑”等等题材且不去说它,连《入厕阅读》(方方)和《美臀》(方希)都写得叫你拍案叫绝。除了题材还有情趣,----煞有介事、正襟危坐的文章愈来愈少了,现在的人活得有滋味,文章也便有了滋味。特别有几种情趣,像幽默和狡黠,像玩世不恭,像傲骨嶙峋,还有另类玩的各种酷。创造的闸门一旦打开,那真是汪洋恣肆!
各种新的散文类型和样式也都涌现出来:社会批判散文表现出来的叛逆勇气和否定精神;文化散文由社会批判转向沉静的民族文化追寻和本土文化反思;生命状态散文将人回归到生存坐标上来审视,同时将环境由客体转化为主体,在宇宙生命体系中展示人生。
潜意识、潜情绪散文在不屈不挠、不依不饶地捕捉自己的影子。将无形却有影的精神世界用文字符号精细地、艺术地表述出来,将以前文字符号没有表述和无法表述的许多生命状态,甚至一些目前还处在生命晦暗地带的精神状态和感情状态,艺术地记载下来,给人类提供了认识生命的新的素材,空前地激活了散文艺术潜在的创造力、拓展了散文话语全新的可能性。
在大众散文、市民散文和小资散文中,平民精神、精英情结、后现代情结通过不同渠道得到展示,酷与俗在发展中合流。而消闲娱乐散文,又使散文由不可承受之轻变成无孔不入之轻。
这一切,决不止是形式,所有的语言方式和写作方式背后,是价值标准,是人生和艺术的追求,是精神状态,是“神”。是“神”!
廿来年的散文写作,随时代生活的变迁,随一代一代作者观念的变化,早已远远超出了“形散神不散”那个时代的话语场和欣赏场。在鲜活的、日新又新得叫人讶异的散文写作实践面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显得是那么苍白。
没有一种以不变可以涵盖万变的说法或主张,总是在蓬蓬勃勃万千变化的创作实践中不断产生新的说法或主张。
大散文和大众散文
大散文把大和散两个字组合到一起,很有意思。大即有散,散亦有大。回归社会,回归大众,不是清理门户,而是开门揖友,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平民情怀,尤其是重视行动着的生活、底层的生活、弱势群体的生活,像《美文》这几年致力的那样。在这个层面,大散文和大众散文有交叉之处。但大散文决不只指题材之广,不只指视角、写法之大,更是指思想之博大精深,这思想之博大精深又不是说一味去宏观思考,而是说要提升思考的质地和质量,是说思考所依托的理念坐标的广大,精神格局的宏大。这其实也就把社会的、精神的大承当作为自己的题中之义了。这当然是一种宏观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大散文和大众散文,虽一字之差,所指、特别是能指,其实完全不同,有时甚至抵牾。
前者提倡、重视散文之神,后者不自觉地销解散文之神。前者提倡关注最大多数平民日常的生存状态,关注社会最广大的底层生活疾苦,在“神”的层面,流贯着一种平民精神、平等精神、人道精神和社会实践精神。也可以说,它所提倡的是世俗化与人文化在散文中的两极活跃,并,构成了生气勃勃的两极震荡效应。后者则往往流于只关注平民生活的浅薄情趣和物质表象。
近年脱颖出一批平民散文家,他们将平民身份、平民心态、平民口气、平民话语提炼、强化,发展为一种新的散文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捅破了多少年来隔离百姓和文人、隔离说话和文章的那层窗户纸,使长期限于文化人专利的散文有了新意,有了生气。但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旨归,我以为仍是人文化的。关注、促动平民生活的人文提升,是他们基本的精神朝向。
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写法:用理性辐射生活,让文章以一种精神境界在文化层广有知音;又用生活熔冶理性,让文章以可读性在现代大众中拥有读者。沉潜着理性的生活流追求并没有耗散了个性,在这里,个性常常不表现为生活细节或语言特征,而是表现为大而化之的眼界、身份、口气、致思方式和感情熔冶方式。
五四散文的“高门槛”和今天的缺失
有人感到,五四散文是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迈过的高门槛。这种感觉我很有点同意(要作为一种论断当然有待论证和完善)。起码从散文和当时时代的关系看不无道理----五四散文对那个时代社会精神和文化精神的凝聚和激扬,至今令人砰然心动。
叫我们砰然心动的东西,最为强烈的恐怕是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那种自由精神的喷薄和作者自由的精神状态。忽中,忽西,忽史,忽今,忽民众,忽神贤,忽社会,忽人文,忽德先生,忽赛先生,窒息千年的民族精神借着他们的笔端大解放、大奔涌、大驰骋。那种气吞万里的气派、博古通今的知识、通达睿智的心态、幽默犀利的笔触,写尽了历史转轨时期中华民族的情怀、中国文人的情怀,是何等的酣畅淋漓。直至今天,还对当前散文构成一种俯瞰之势。
再有便是五四散文中的人文精神。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总体上进入现代层次。有对人生遭遇和命运纠葛层面的关注,不但关注民族的、大众的共同命运,也关注个人的、甚至是异态命运、异态人性。既关注“大写的人”,关注那个神圣者、崇高者、先进者、成功者系列,也在那个时代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关注 “小写的人”,关注平民百姓。有时更超出了状写人性美和人性恶的层面,即观察和展示的层面,而着重以一种深虑思维洞烛幽微、深入腠理地对民族文化人格进行反思和建构。这些散文在人性的美丑面前褒贬鲜明,充满扬善抑恶的激情,又有着文化积淀带来的宽容。宽容背后是冷静到冷峻的思索和剖析,节制出于素养而入于境界。
在激扬自由精神和对人性、对生命的体察和思考上,五四散文可认说是和五四时代交相辉映,同步辉煌。
这是五四散文所以门槛高的原因,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当下散文的缺失。缺失提示着希望。
兴起的都市情怀和变异的乡村情怀
乡村情怀仍旧是当下散文的一道精神景观。而都市情怀的大量出现和向乡村情怀的渗透,也许更值得重视,更有感情和思考的信息量。
写童年和老人,写小路和小路尽头的远村和土地,依然那么富有魅力。但这种魅力已经远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乡村情怀。那时散文的乡村情怀主要来自作者个人命运与乡村生活的纠缠,主要表现为村社文化对第一、二代农裔城籍者残余而又执拗的影响。我们从中能够看出现代中国人在精神上是怎样一步一回头地、趔趄着由农村走向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的。
当下散文的乡村情怀依然包含这些内容,但主要意蕴已经发生变化。农村生活、乡村情绪对农裔城籍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来说,已经十分遥远,和他们命运的具体关联也已日渐依稀。土地于是在相当程度上泛化为大地,乡村更多地升华为一种精神和感情的彼岸,而和他们的都市生存现实的此岸相对应。乡村多少被理想化、象征化了。
这一代散文作者的乡村情怀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作为当代都市生活超速节奏、超量信息、超重压力、超载心理的一种缓冲、淡化和消解因素。对应着现代城市生活的各种弊端,作者给已经进入历史记忆的乡村赋予了各种幻影幻觉,现实的乡村被审美化之后,像海市蜃楼留存在日益浮躁的现代人的心头,起着清凉油的作用。
二是用现代都市意识和都市情怀重新诠释乡村。这类散文中的“乡村”和“乡村情怀”,已经被文化化为传统、经典、精神家园、生命归宿的词语代码,进而又生命化为阳光、空气、水质等象征着恬谈、冲和、出世人文观念的词语代码。
当下散文更重要的特点,也许是都市情怀这道景观。大都市是现代文化的产婆,都市情怀也就是现代情怀。中国进入了现代大都市集群性出现,现代都市文化逐渐走向成熟的年代。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新都市景观、新都市社区进入过我们的散文;也从来没有这么多各阶层市民生存状态、人际关系和心理意绪进入过我们的散文。所有这些,都是过去散文中很少见到的。不论质量如何,这本身就具有原创价值。
都市情怀散文,有下面几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人的活动、人的价值观、人的感情和意绪的表现。市场经济的生活世相和现代人的“活相”,集聚了大量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新信息,使都市情怀散文有了沉甸甸的份量。
在世代血统市民日益成为城市主体,都市文化积淀开始形成风格,并且初成传统的时候,散文中的都市景观已经上升为一种都市“乡村”情怀。第一、二代市民在城里生活的那种“无家”、“无根”的感觉正在消逝,人和他周围的水泥森林一样,开始在城市扎根,找到了一度失落的精神家园。城市已经转化为新一代人的“乡村”和“土地”。他们对自己居住的城市产生了一种“乡情”,这种乡情如他们的父辈对村庄的感情一样,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归属感。
都市乡情散文对白领生活和白领情趣的抒写,是当下散文一个新的领域。“白领”作为人群的界定是模糊的,但作为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的界定却较为明晰。这是一群不为物质生活所苦因而看重精神追求的人,是一群不用为生计奔忙因而可以讲究生活情趣的人。他们在城市霓虹灯下或靓,或蔻,或爽,或酷,生活得舒适而有格调。现代市场,尤其是跨国资本颐养着他们,他们的格调和情趣天然地带着洋酒“×○”的色香味。当代散文所传达的“白领”情调,在城市和青年读者中极有市场。商家(包括出版商和报刊书商)尤为好看。因为“白领”情趣给正在步入小康的中国人一个可望而又可即的梦。这类散文以超前享受的梦幻,刺激消费欲,膨化购买力,使读者由潜在的消费群体迅即转化为现实的消费群体。
近年来兴起的大生态文化散文,比之乡村情怀和都市情怀,格局是更大了。这类散文,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落笔,抒写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内涵,抒写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人文范畴,而由人文文化进入了生文文化、地文文化、天文文化,当然最后又总是回到人文文化的大气层中来。我们从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命空间和文化空间,感受到作者以一种生命脉冲逼入物象本质的精神力度。
要警惕“伪我”,要“我”中有“们”
原生态散文近年有发展,伪经验、伪情感、伪想象的问题比小说要好,生态散文、行走教文、底层状态散文以及一些私人话语的散文,都是散文界追求文学真态的表现。但也要警惕集体经验对个我精神的挪移和置换。时兴的小资散文、娱乐休闲散文、身体写作散文、私秘散文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雷同,其中便埋藏着集体经验在个人心理中复制的倾向。当下中国的许多时尚,不仅有这块土地上的集体经验,还大量隐藏着西方的集体经验。西方的集体经验通过“文化普遍主义”开路,蚕食我们的民族精神,甚至取代部分人的内心世界。本来是“我们”的、“他们”的,有人却误信为是自己的、“我”的。这个“我”其实是“伪我”。创作出现伪经验、伪感情、伪想象,其因盖源于此。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散文家一定要积累亲身体悟过的、原生的文化心态、感情意绪、理性意识,用来作为自己文章的“神”。这种“神”是只属于“我”的,但“我”中又必然溶解着“们”:或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或是时代发展和世界进步最优秀的精神成果,通过“我”的有个性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表现出来,使我们的散文具有精神的和文化的质地。我想,再怎么说这也比挪移和置换他国、他地、他人的理性和感性经验,以“伪神”为神、以“伪我”为我要有价值得多吧。
《香港故事》研读,确是小处入手,语浅情深,可见作者的真性情。于是选了三篇精短的散文印发给学生预习,让他们从中感受情意,揣摩写法。读着她所叙述的一个个“香港故事”,我们感受到的是她内心涌动着的历史悲情。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不难理解她对香港这样一座身世朦胧的城市的爱恨交缠的复杂情感。 |